玉米的傳播
明代文獻中記載的玉蜀黍
(2)

天野元之助氏嘗追蹤玉蜀黍栽培地區的展開過程,欲求闡明玉蜀黍在中國境內的傳佈途徑,其結果不一定可說是成功的**,在比較新近的歷史時代引入中國的作物,在各地方志中,其內容縱或不一定十分正確,但皆帶有說明,說是外來的。
天野元之助1962中國農業史研究。p. 53~58.
一般傳說是由於張騫傳入的西瓜葡萄,時代很古老,栽培很普遍,在方志中,大抵皆不載來源。但可視為與玉蜀黍同傳入的美洲大陸原產的作物如馬鈴薯、甘藷、落花生、煙草等。則在各地方志的物產部中,大抵皆附記其來源。試舉數例如下:
「淡芭菰」種出東洋。莖葉皆如秋菊而高大。邑人多植之,切為白絲,蜀中之名品也。稱曰白煙。(四川遂寧縣志,一七八七)。(于按:遂寧縣志文是據日文譯出,未及對照原文。)
「番藷」一名甘藷。根葉皆可食。其種有朱者,有白者,有皮肉俱紅者。明萬曆中得之呂宋國。凡沙礫之地亦皆可種,不甚費人工。(福建漳浦縣志卷二,1700)。(于按:漳浦縣志文,嘗覆按原文。是民國十七年翻印本,有康熙三九年序,原序年號作嘉靖。)「馬鈴薯」洋種傳來,亦合土宜。(福建建甌縣志一九二八)。(于按:嘗覆按原文。)「落花生」為南果第一。以其資於民用者最廣。宋元間與棉花、蕃瓜、紅薯之類同為粵估自海上諸國得其種歸種之。……落花生曰地豆。……今已遍于海濱諸省(檀萃,滇海虞衡志)(于按:嘗覆按原文。)
即在中國方志或其他記錄中,對於新來的作物,大抵皆傳述其由來。如玉蜀黍是由同樣方式傳入,則似應有同樣的記錄。但是,祗有玉蜀黍,在本草書中,是說來自西土或西番。這究應如何解釋?如籠統地說是因民眾沒有傳述正確的知識,似不能說是一謹嚴的解釋。要之,至少就玉蜀黍這一農作物言,在中國方志中,絕對沒有絲毫跡象說是由萄葡牙人自海道傳入。筆者不明白玉蜀黍之傳入中國,為什麼一定要與葡萄牙人之東來聯結在一起?或一定要規定玉蜀黍是由哥侖布方引入舊大陸?如有明確的根據,布望讀者仍提供。
如果沒有根據,則在現在的常識上縱或是可笑的異說,似亦有加以檢討的必要**。玉蜀黍的乾燥種子,一個旅行者可攜至很遠的地方,故其栽培地很可能分散作點狀。至若某處的居民完全食用玉蜀黍,玉蜀黍形成為定居農耕文化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則大概是要相當長的期間。
例如Swingle謂中央細亞的回教徒在十六世紀中葉由麥加傳入新疆或西藏,而由此傳入中國本部(W.T. Swingle 1934 Maize in
China. Nature, 133:420.)。關於這一見解,筆者是不同意的。
若作為珍奇植物之一而予以栽培,則其栽培是有限度的,縱或一時性地可成為特產,而要繼續發展成為產業是須要著各色各樣的條件。據此觀點,則在方志類中,止於一州一縣的小域時,在量方面,可說尚是不安定的。例如正德顈州志的記載,在後代的物產項中,是把玉蜀黍除去了的。如果不止於一府一縣,例如在各省的通志中,其栽培涉及於廣大區域者,則對於其開始記載的時期,應可視為在該一時期該一作物栽培已久、並已安定的證明。
中國的玉蜀黍這一正式的名稱,是由『本草綱目』而方為學術界所知道的名字。在『本草綱目』之前,是稱番麥,即以為麥的一種。或稱包粟、珍珠粟,而視為粟的一部分。此外尚有苞米、棒子、玉榴等俗名。至如觀音豆,雞豆粟的稱呼,則如無預備知識,實無法想像其所指者為玉蜀黍。但是根據該項名稱,要確定其為玉蜀黍,有時是有困難的。例如吳其濬的『植物名實圖考』長編引直省志書,把當時普遍的名稱玉麥、番麥,皆包括收錄在麥的項下**。
中國以蕎麥亦納入麥類中。故中國之所謂麥,大概是汎指磨粉後食用的穀類。中國人以前對於玉蜀黍大概亦是磨粉後食用,故亦稱曰麥。玉字大概是因其穀粒的光澤而來。雲南大姚縣志曰:「其用適與穀麥無異」。
至最近的中國農學遺產選集,則畢竟是不同了,不再誤以為麥。但『五穀史話』中所記中國各地方志中的有關玉蜀黍的名稱,究竟以什麼根據決定其為玉蜀黍,則不無若干疑問。例如被視為中國第二部最古的方志,是1531年刊行的嘉靖廣西通志(在日本內閣文庫中不是有此本),其中有語曰「稷俗名明禾」。『五穀史話』以為指玉蜀黍。其根據何在,並無說明。
在萬曆太平府志中有語曰「稻,太平之人名曰畬禾」。這是土人以稻(大概是旱稻)與普通的燒田(畬)作物相區別的名稱。廣西通志謂「稷曰明禾」者,大概是因土人本來種的是其他的雜穀,而新來明人將稷攜入,故稱明禾。這稷,按傳統的解釋,是指後人所說的粟(Setaria),據後人轉訛,是指高粱(Sorghum)。
其次,在臺灣出版的明代方志選中,有萬曆廣西通志。其中不見有相當於玉蜀黍這一作物的名稱。『五穀史話』究屬有何根據決定謂明嘉靖時在廣西已有玉蜀黍,其說殊不可解。同一皇朝的皇帝的交替,而重修一個地方的方志時,對於前代的方志,完全不加參考,大概是不可能的。
要之,在『五穀史話』中,檢討各地方志的物產的結果,在明代有玉蜀黍者,是有河北、山東、山西、河南、陜西、甘肅、江蘇、安徽、廣東、廣西、雲南等十省。在此處,有一點值得注意,即:玉蜀黍如果是由南海路線傳入,而在明代的浙江福建二省的方志中,卻不見提及玉蜀黍之名。但田藝蘅是浙江人,李時珍是湖北人,田李二氏已在其鄉里實在看到了玉蜀黍,故在明代末葉,不妨視為玉蜀黍已散佈於中國的全境。如謂玉蜀黍之傳入中國是在明末,並祇有南海一條路線,則在短期間內,其散佈會如是之廣,是不很容易使人理解的。
在另一方面,如欲根據地理分佈,以求知其傳佈的途徑,則根據方志的省別的分佈,不很容易進行研究。然如根據州縣的記錄,以推測栽培集中的程度,則或可據以推測玉蜀黍在某一區域的栽培時期的長短,即或可推測某一區域引入玉蜀黍的遲早。又如同一地方的方志,連續記載有玉蜀黍,則可推測其栽培量多,若在舊志中有而在新志中消失,則似可推測其栽培量減少,而已失去其重要性。據此原則,則在十六世紀中葉,已廣汎地栽培玉蜀黍的,有雲南省的大理、蒙化、永昌、鶴慶、姚安、景東等六府,即金沙、瀾滄、怒江三大河自西藏高原流出而將要分開時高原區域,似為集中栽培著玉蜀黍的場所。
上述區域之各地區中的詳細的分佈,則要到後代方纔明白。惟在該一區域的大部分的縣志州志中,皆記有玉蜀黍,其說明亦極為詳細,故似可推測玉蜀黍是很早已在該地普及的作物**。該一地區緊接於所謂西番之南,而是在西番與明代苦心討伐的金齒、平緬、芒巿等蠻族諸衛之間,故在中國本土言,是很容易與所謂西番相混淆的。
雲南許多縣志,對於玉蜀黍的說明極詳細。上述大姚縣志,對於作為食物的使用方法與栽培法,皆說明極詳。
西藏有諺語曰「有犁牛處不長玉蜀黍」**,真正的西番,例如青海,溫量指數不足,玉蜀黍的發育困難,故作為玉蜀黍傳入中國本部的傳佈基地,無基意義,是一如De
Candolle之所指摘。
據中尾佐助教授的指示。
De
Candolle是不承認玉蜀黍西番起源說的。事實上,在四川西部的藏族居住區,到清朝末期為止,玉蜀黍尚未傳入**。
四川松潘紀略(1873)記有栽培經過。
但是,湄公河上游原在人民的秤戛野人的區域,是在乾隆十五年(1750)方併入清室的領土,其染齒成黑色,面上亦塗顏色,而其人是以包穀,即以玉蜀黍為常食。稻及其他作食糧用的植物,栽培極少**。故吾人當可承認其很早已將玉蜀黍包攝於其農耕文化中。縱令說哥侖布自美洲將玉蜀黍攜歸舊大陸,再傳入廣東,試問是誰再將這種子傳入如此偏僻秘奧的地方?
漢軍:滇南新語,收錄於小方壼齋輿地叢書中。
上述栽培玉蜀黍的區域,不是西藏貿易所經由的道路,故由回教徒經由新疆而搬運的可能性極少。除開與緬甸北部的原住民作種子交換以外,該一區域的居民,大概沒有其他方法可獲得該一植物。因為在該一時期,以中國本土言,湖南、湖北、福建、四川等省,尚有很多地方不見有玉蜀黍的栽培**。如上述推理是正確的,則該項野人栽培的玉蜀黍的品種,大概不會是由葡萄牙人東傳的Caribbean
Type。關於這一點,今後的野外調查,大概是會證明的。
參閱湖廣通志、四川通志、福建通志。
在雲南西部高地分佈甚密的玉蜀黍的栽培,究係始於何時,現尚不明。但栽培遍及於四萬平方公里的山地全境,其傳佈決不是一短促的時期。葡萄牙人到達印度西岸是在16世紀初葉,而中國文獻中有玉蜀黍出現,是在16世紀中期,這短短的50∼60年會傳佈如是之廣,實很難想像。因就當時的玉蜀黍言,與稻及當地已有的旱田食糧作物競爭,玉蜀黍實在不能說是一豐產的作物。
關於這一點,稍後另當有說。但雲南栽培玉蜀黍,亦決不能說很古,故亦不能考慮其為玉蜀黍的原產地。例如樊綽的蠻書,關於雲南的農耕,記述頗詳,而沒有提到玉蜀黍,續雲南通志稿中記有原住民的方言,如稻、大麥、小麥、燕麥等主要穀類,是列記著夷族、泰族、白族、儸儸族等主要種族給予該項穀類的名稱。但對於玉蜀黍是祇舉示儸儸族、白族的Zhou-mo而其他種族皆無相當於玉蜀黍的名稱。這是指示著玉蜀黍的傳佈尚未普及於全部的原住民而似是一比較新的作物。
在記載明末清初的物產的直省志書中,玉麥之名是見於河北省清苑縣、山東省歷城縣、河南省昌邑縣、延津縣。在現在,玉麥之名,在雲南省,是限於西北部;在省城昆明,是稱包谷(包穀),這是由貴州擴展到雲南的名字(24)。其他如四川省西部,亦尚留有玉麥之名。據此以觀,玉麥之名,在中國,嘗廣佈於各地,而現在是殘留於偏僻的地區。
北京大學中國語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 1964漢語方言詞匯。
在清初,有玉麥的地方,現在是稱棒子或包穀,這是指示著後代的新的名字壓迫著舊名玉麥,而使之趨於消失。又如江南地區通稱的番麥,現在袛是殘留於福建廈門、同安,而江南卻是用俞賣(于按:當是玉麥的寫音)棒頭等新的名字**,此項方言變動的原因之一,或可考慮是因新品種出現,代替了舊的品種,因此聯帶著使舊的名稱消失。例如雲南本來的舊品種的玉麥,因有稱曰包穀的豐產的新品種自貴州進入昆明,與昆明之西的玉麥區域楚雄接觸,其結果,在楚雄地區是產生了新的名稱曰包麥。十九世紀末期雲南地區有關玉蜀黍的方言的分佈是如第三圖所示。
湯起麟,玉米p.1,列示苞蘿、六谷、玉茭等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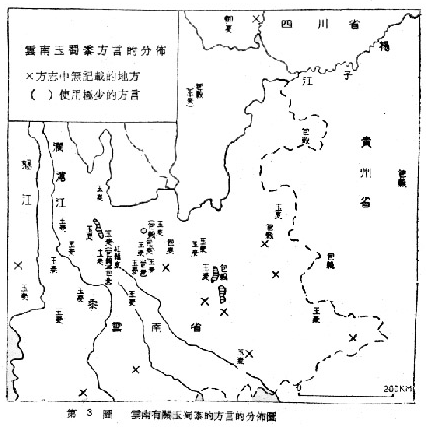
在道光二十五年(1843)的姚縣志中,並舉玉麥與包穀,而列述二者之異曰:「包穀即玉蜀黍,一名玉高粱。其狀,莖如甘蔗,高七八尺,每節葉間出一苞」。「玉麥似甘蔗而矮,每株二三苞不等」。南寧縣志引道光十五年(1835)的雲南通志稿曰「大麥小麥燕麥三種植於陸地;玉麥植於園中,似蘆而矮」。據是則所謂包穀與玉麥,似是在高度上有著差別,即包穀高而玉麥矮。就野外觀察的觀點言,似可推測這是Caribbean
Type 與Persian Type之異,而大概在產量上亦有著差別**。
Caribbean
Type玉蜀黍的典型,見於寺島良安的和漢三才圖會。這可視為葡萄牙人自Caribbean sea攜來的系統。
在光緒二十八年(1902)的績雲南通志稿中,有很值得注意的記載。其言曰:「謹按,玉麥形似包穀,惟其苞大而子實小,不成行列。」據此以觀,可說:稱曰玉麥的玉蜀黍系統與子實排成行列的Caribbean系統。在系統上顯然有別,又玉麥的粒色有藍紅等,且多糯的品種;而屬於包穀的系統,其子實有黃紫瑪瑙等色,而大多是硬質,或似齒粒種**。
湯起麟,玉米,p.2。
子實小而排列不整齊的玉麥,每株的苞數少,故其產量大約不高。至稱曰包穀的新品種,是由東南進入,每一節葉間有苞,自高度以觀,可推測其為Caribbean
Type**,其產量高,故似很快就普及於各地。此項推測,將來的實地調查,將可證實。儘可能的文獻的研究,當可在作實地調查前,先建立一項工作假設(working
hypothesis)。
大姚縣志曰:「每節間出一包,如冬筍。綠籜數重裹之。籜似竹而軟,中有胎,如茭筍,根大而末銳,其格如之房子,格中居然有蛹土在,平鋪密綴,如編珠然,初含漿,漸實漸老,或黃或白或紫或赤,五色相鮮,籜顛吐鬚,如絲如髮,色紫而絳。每莖或四五苞,或二三苞。莖頂有穗。正似薏苡。」據是以觀,可知稱曰包穀的系統,決不是如『本草綱目』所示玉蜀黍之于實裸出的系統,並與玉麥似的子實不成行列者亦不同。(于按:本節中所引方志文,皆係自日文譯出,不獲與原文對照。)

|